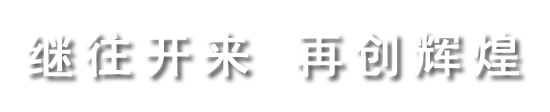数字治理孙艺珂:自由与认同:数字游民文化与本土化社会实践研究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游民这一群体在中国逐渐壮大。他们试图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在身份认同、整体自主性和社会互动等方面建构自己的生活哲学,其社会实践可被视作一场大型生活实验。社会化媒体等载体孕育和强化了数字游民的身份认同与集体归属感,他们解构传统工作观念,秉持新工作主义理念,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数字游民的地理套利行为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也可能改造传统乡村生态。数字游民的发展尚处于探索期,其结局是找到人生的旷野还是回归主流 ,仍未可知。
目前,慢慢的变多的人开始探索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数字游民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群体,正成为这种探索的代表。他们冲破传统的职业束缚,选择了一种灵活的、不受地理限制的工作方式,以此应对现代职场的高压和不确定性。本文旨在探讨数字游民如何寻找新的身份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如何反映出个体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追求,并与传统社会结构相互作用。
“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描述的是那些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远程工作,并选择经常更换居住地或在世界各地旅行的人(Thompson, 2019)其与背包客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工作和生活方式。背包客通常是在旅行期间休假或暂停工作,而数字游民在旅行的同时工作,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获得收入(Stumpf, Califf & Lancaster, 2022)。数字游民与传统远程工作者也有所不同:传统远程工作者一般为他雇者,拥有定期收入,倾向于在一个地点生活,往往缺乏社交活动(Matos & Ardévol, 2021);数字游民则追求更高的自主性,希望可以自主选择自身的工作项目、上班时间和居住地。数字游民主张,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领取报酬的多少,更能反映真实的社会等级(Cook, 2023)。
德勒兹(G. Deleuze)、萨特(J. -P. Sartre)和马尔库塞(H. Marcuse)的理论,为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思想基础。德勒兹倡导的流动性和去中心化理念(Yang & Yang, 2009),萨特存在主义理论中的个人自由与责任(Glendinning, 1999), 马尔库塞对一元化思维和消费文化的批判( Peñaranda,2013),共同构成了数字游民价值观的哲学框架。这一框架鼓励个体超越传统模式,通过行动进行自我定义,同时利用技术解放潜力,探索自由和灵活的生活与工作方式。
追溯西方数字游民的历史源流,有两个脉络:工作模式上,背包客逐渐转变为收入型旅游博主,利用数字技术和社会化媒体进行内容商业化,互联网远程工作者的兴起也实现了工作与旅行的融合(Makimoto & Manners, 1997);价值取向上,贝格曼(F. Bergmann)的新工作主义理论、费里斯(T. Ferriss)的《每周工作四小时》和格雷伯(D. Graeber)对现代工作的批判,共同塑造了数字游民对新工作和生活观念的接受和实践。
既有研究涵盖了数字游民的多重身份认同、选择居住地点的影响因素、生活方式实践、与传统环境的互动模式等多个角度。这些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字游民做出详细的调查,揭示这一群体的特征和行为模式。
数字游民的身份认同是多元的。已有研究之后发现,社会化媒体关于数字游民的叙事有四种:浪漫主义者,强调数字游民生活的自由和灵活;现实主义者,强调数字游民生活的实际难处;机会主义者,主要关注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商业化机会;理想主义者,认为数字游民生活是人生的最佳状态(Ehn, Jorge& Marques-Pita, 2022)。这些类型化的叙事塑造了数字游民的集体认同。数字游民的身份认同也是流动的,他们通过符号性消费建构自己的形象和流动主体性。对他们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既提供了身份转换的机会,也蕴含着自我实现的意义,是人生阶段的一个过渡。但是,这种生活方式也存在财务风险和永久边缘化的可能(Louis & Mielly, 2023)。
在选择居住和工作地点时,数字游民重视目的地的自然文化资源、基础设施条件、生活成本以及信息网络,这也是一些热门数字游民聚集地的关键吸引因素(De Almeida, Correia & De Souza et al. , 2022)。数字游民对联合工作空间的高质量服务和设施有着浓厚兴趣,这凸显了他们在选择工作地点时对环境的特殊关注,而远程工作的增加也为他们创造了新的机遇(Orthaber& Zupan, 2021)。数字游民试图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有研究提出了数字游民个人创业的阶段性模型(Louis & Mielly, 2023)。此外,克罗地亚政府为吸引数字游民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公司管理层在整合数字游民时面临的挑战,均表明了主流社会对这一群体需求的理解与适应( Gorlińskiucik, 2021)。
中国的数字游民受民间传统文化和个人主义影响,有独特的发展路径。在实践数字游民生活方式时,他们没办法享受到与之匹配的全球化工作机会、远程工作政策和高社会接受度。因此,从概念旅行的视角开展数字游民本土化研究有其必要性(姚建华、杨涵庚,2023)。
本研究对 98 位数字游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结果得出:数字游民群体性别分布平衡,男性占比为 54%,女性占比为 46%;普遍年轻化,25—34岁的数字游民占比为 57.14%,这一阶段正是职场黄金年龄;大多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95.92%),其中本科学历占比为 68.37%,硕士学历占比为 27.55%,教育资本积累程度较高;一致认为自己“不受人管辖,思想独立”(78.57%)、“怀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56.12%);成为数字游民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追求自由和独立( 96.94%), 其 次 为 对 传 统 工 作 方 式 不 满 ( 59.18%)、 追 求 更 高 收 入(26.53%)。数字游民追求高度的个人自由和灵活的工作模式,主要涉及互联网相关行业及创意产业,可见他们在新兴起的产业中的活跃度和在传统行业以外的开阔视野。
数字游民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展示旅行经历和生活实践,以建构和巩固身份认同。在社会化媒体上,最能代表数字游民的画面应当是:迷人的自然风光做背景,笔记本电脑屏幕做前景,画面的别的部分不经意间展示出本地特色美食或其他标志性地理符号。这种自我表征机制强化了他们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和自豪感,并以此为“暗号”连接全球数字游民,强化自我身份感。尤其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这种展示强调了他们作为全球公民的身份特征。美好生活的媒介展演既是对所选生活方式的自我肯定,也引发了围观者对数字游民生活的向往和传统工作模式的反思。
数字游民的身份认同具有流动性与多样性特点。数字游民在社会化媒体的虚拟空间中叙述个人经历,进行视觉呈现,构建了一个多维度、动态发展的个人形象。他们在自我表征时频繁使用不相同标签,涵盖生活方式、职业兴趣及文化经历,反映了身份的流动性与多样性。例如,李明(化名,下同)的个人介绍中有自由撰稿人、环球旅行家、摄影爱好者、环保志愿者等多个标签。他展示了在不同国家的旅行经历,如在泰国拍摄日出照片、在西班牙参加当地的节日庆典,以及在印度参与环保活动。在职业社交平台上,李明强调他自由撰稿人的职业身份,分享他为多个国际杂志撰写的文章的链接。通过这一些不同的标签和社会化媒体平台,李明的自我呈现出流动性与多样性。
相较于西方的数字游民,中国数字游民更倾向于通过社群获取社会支持和认同感。长期维持数字游民生活对个人生存能力的要求很高,而参与在线社群则是一条寻找可持续生活方式和职业的路径,也是一种减轻经济压力、提高职业成功率的策略。在数字游民面对更多挑战和不确定性时,共居社区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资源。
数字游民共居社区是一种新兴住宿模式,整合了居住和办公的功能。社区内一般配备了完善的办公设施,有相应的社交活动区域,以满足成员独立工作的需求及与其他数字游民的交流合作。此外,共居社区还是个体自我发现和集体身份构建的重要场所。每一位成员在申请入住时都要提交一份答卷,社区主理人基于申请人的教育水平、职业经历、兴趣爱好等背景筛选合适的候选人,以保持社群成员间的异质性。筛选出的数字游民个体在社区中极易获得群体共鸣,社区中的社交互动则进一步强化了自我与社区集体之间的联系。例如,A 社区每周一晚上举行“思享厨房”活动,社区成员自我介绍并相互认识;B 社区每周六举行人工智能(AI)工作坊,教零编程基础的数字游民学习使用 AI 工具;C 社区不定期举办小众电影观影分享活动;D 社区每周三下午举行小型分享会,分享人互相交换技能和需求。
在共居社区中,我们抱着一种开放和坦诚的生活态度。每当有新成员加入,我们都热情地欢迎他们,认为他们带来的一切都是对我们社区文化的丰富。我们之间的交流始终坦诚直接,大家都乐于分享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如果你需要帮助,或者有能力帮助别人,我们总是愿意坐下来讨论,寻找最佳的支持方式。这种互相支持和坦诚沟通的氛围,是我们共居社区的核心特质。(D 社区主理人晓薇)
我们的共居社区每周五都会举办一次名为 Foodie Friday 的活动,邀请所有伙伴参与。这是一个社交和学习的机会,大家在这里相互认识,可能会一起学习制作咖啡,或者讨论数字游民生活相关的话题。同时,我们也会向大家介绍并请他们尝试各种植物性食品。比如,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常见的水果的独特吃法,有时会做水果吐司,或者把香蕉做成奶昔。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增进了社区成员之间的了解和交流。(C 社区主理人雨欣)
数字游民的生活哲学不限于单维度的自由,更关注在经济、时间、兴趣爱好、居住地选择以及社交关系等多个生活领域中的整体自主性。数字游民追求的自由可分为五个维度:经济自由、时间自由、志趣自由、居住自由和情感自由。经济自由包括收入自由和支出自由,前者指想赚钱的时候就能赚到钱,后者指不会因为金钱的匮乏而没办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时间自由并不是无所事事地“躺平”,而是有自主分配时间的权利。志趣自由是数字游民最典型的特征,也是最容易实现的目标。数字游民摆脱传统价值观的束缚,自由选择喜欢的事情。居住自由即根据自然、人文、社交、物价、签证等因素选择“游”到哪里。情感自由经常与社交资本相混淆,本调查显示有 61 位数字游民感到孤独,有情感支持和归属感方面的需求,他们渴望与他人进行深度交往。
李华是一位远程工作 8 年的 IT 工程师,通过在线项目协作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赚取收入。他为维护客户关系,工作的时候比在办公的地方里更加投入。王芳这样的自由撰稿人能够准确的通过自己的生活节奏自主安排工作,选择在清晨创作,下午休闲,从而平衡工作与生活。旅行博主兼旅拍摄影师张强,能够将个人爱好与职业相结合,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谋生。赵怡然选择在大理、清迈、巴厘岛、里斯本等地生活和工作,探索多元文化。区块链从业者经常参加国际黑客松或快闪城市活动,在活动期间共居共创,建立全球性的社交网络,遇见志同道合的朋友,丰富个人和职业生活。
数字游民视新工作主义(new workism)(Bergmann, 2019)为圭臬。这一理念的核心在于重构工作的意义和方式,强调在工作选择和方式上的个人自主性,并寻求工作与生活更好的平衡。这一理念鼓励工作模式创新,如远程工作和自由职业,反对传统集中式、等级化的工作结构,倡导更分散、去中心化的工作环境。蒂莫西·费里斯(Ferriss, 2007)提出了“设计生活方式”的理念,即根据自己愿望和目标主动设计生活,而不是完全被工作所左右,同时利用地理套利来提升生活品质,并通过时间和财务管理实现更多的自由和独立。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Graeber, 2018)则从批判的方面出发,认为现代社会中大量的工作毫无意义,这些工作往往使人感到自己的劳动毫无价值。他对传统的工作伦理提出了疑问,认为工作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工作本身,而应该是实现个人价值和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手段。
数字游民的生计方式多种多样,基准线是自给自足。从全职工作到自由职业,从股票投资到资产管理,各式各样的途径共同构成了他们经济生活的多元图景。在这些方式中,自由职业者更受益于互联网零工经济的兴起。他们最具有数字游民的特点,利用互联网平台接受各式各样的零工任务。远程工作的数字游民,其职业生涯相比之下更为稳定。然而,稳定并不代表轻松。为了保持这种稳定,他们必投入相应的时间和努力,这往往意味着必须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由于远程工作的特性,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二者常常交织在一起。
数字游民的经济来源主要有四种:劳动收入、流量收入、创意收入和资产收入。首先是劳动收入。远程工作者,以工资维持生计。佟彤是一名时尚杂志编辑,供职于上海某公司。她和母亲住在一栋白族村民的院子里,定期出差,其他时间远程办公,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上海的高薪资水平和×市的低生活成本,让佟彤的幸福指数飙升。比起都市的快节奏生活,她在×市可以用半个月的时间参加戏剧社,每周参加摇摆舞会,给其他舞者拍照,并获得“百万摄影师”的赞誉。其次是流量收入。志成原是一名企业销售人员,爱好摄影,新冠疫情期间来到×市,成为旅拍博主。旅游旺季的时候,粉丝受其吸引成为客户,同时他还获得内容流量本身带来的广告商单。再次是创意收入。明炫曾在海外学习戏剧,他在×市发起疗愈喜剧工作坊,以戏剧的方式帮助参与者摆脱生活中的尴尬,工作坊报名费为 298 元/ 人。最后是资产收入。×市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些数字游民通过经营民宿、酒吧、创新教育学校等方式获得收入,也有 Web 3.0从业者从虚拟资产交易中获得收入。刘健是一位经验比较丰富的数字游民,早期生活在清迈,曾开过一间网红咖啡馆,买咖啡的人半夜还在排队。新冠疫情期间,刘健来到×市,在一条主干道边开了一家酒吧,同时为数字游民共创活动提供场地支持。
数字游民脱离一线城市紧张的工作节奏,来到×市难以维系之前的收入水平,“即使原工作模式转入远程办公模式,在薪资水平和职位晋升方面也会受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影响”(数字游民 Tina)。有相当一部分数字游民脱离原来的工作岗位之后能凭借原工作技能成为自由职业者,或者放弃原来的工作内容而开启新的事业。小薇曾经在外企和商学院工作,开始数字游民生活后决定将人生教练(life coach)作为自己的新职业。尽管人生教练在国内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但了解并愿意为之付费咨询的人寥寥无几。在新事业起步阶段,小薇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大不如从前,甚至需要另外的收入补贴。
在数字游民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间隔年( gap year)学生或刚刚毕业的应届生,没有工作经验和积蓄,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父母补贴,因此数字游民的生活在带给他们精神自由、生活愉悦的同时也带来了金钱焦虑。2000 年出生的李磊本科毕业后来到×市,他本人从未上过班,凭着对电影的一腔热爱,又恰逢 AI 绘图工具技术成熟,受惠于零工经济,他利用互联网接单为客户制作 AI 动画。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认为还要一份稳定的收入,因此在旅游商业区某酒吧谋得一份工作,以此缓解自己的金钱焦虑。自称数字无业游民的陈曦正处于科研间隔年,因为经济不独立而经常与父母产生摩擦,争执的核心是父母希望他早点毕业找份工作。陈曦的男朋友在某世界 500 强企业工作,在陈曦的鼓动下准备辞职成为数字游民。由于工作年限短,积蓄只够两人生活几个月,辞职之后的生计问题也让陈曦的男朋友有些焦虑。
数字游民经常有金钱焦虑,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而放弃这种生活方式。陈曦认为她和父母、男朋友的矛盾点主要在于金钱,而她本人从来就没赚过钱,也没有赚钱的经验,对自己能否赚到足够的钱没有信心。她希望能够通过做自媒体来寻找一些变现的机会,抓住一切机会寻求经验。本硕博一路连读的小雅没有工作经验,在同龄人都成家立业的年纪,自己还没办法实现经济独立,无法赚钱是当下生活状态唯一的缺憾。有趣的是,李磊、陈曦和小雅都没有因此终止数字游民的生活状态转而去工作,陈曦甚至还劝说男朋友辞职成为数字游民。由此可见,金钱焦虑似乎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生活志趣,于他们而言这不过是人生探索期的阵痛,他们对走出金钱焦虑充满信心。“我说的‘希望被资本收买’也就是口嗨一下,要是真被资本收买了,我可受不了。” (数字游民小雅)
数字游民重构生活和工作模式,采取远程工作、自由职业等灵活多变的工作方式,以游牧的生活方式对抗创造物异化和创造过程的压力。“游牧的核心在于对在场的超越。我们所推崇的游牧主义,是勇于打破系统、结构、疆界的束缚,是对边界和可能性的探索,是对创造性、想象力的思考。” (数字游民映雪)不同于“躺平”,×市的数字游民强调自我实现,超越职业成就的界限,探索个人兴趣和生活方式,从而减轻社会规范和期望带来的心理上的压力。他们追求内在满足而非外在奖励,注重工作和生活的本质意义,这种内在导向的生活方式促使他们真实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个性。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数字游民的内在自我区别于荣格(C. Jung)的意识自我( ego),并非只关注自己的感受,他们将社会公共价值纳入自我实现的范畴。例如,小晴曾是一名公办中学的数学老师,跟随某公益组织来×市支教,服务期结束后继续留在×市。
数字游民通过社区和支持网络,寻获精神和情感上的互助,以共同体的形式抵御社会压力,增强内在自由和自主感。他们旅行体验多样生活,打破单一文化或观念的束缚。他们摆脱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理论中“组织的人”和“一维的人”的境遇,展现了从“他定型”的人向“内定型”和“普洛透斯式”的人的转变(科恩,1986)。这种变化反映了个体思考自我存在的象征概念的稳定性,以及对新文化象征的接受。“我前 7 年在中国最好的大学读书,从小一直是别人眼里的好学生,我想撕掉‘好学生’的标签,寻找自我。”(数字游民黑马)“我想对生活有更多的掌控,撕去外界的标签,进行注意力管理,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减少外界对自己的影响。”(数字游民 Candy)
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体现了鲍曼(Bauman, 2000) 所描述的“液态现代性”,即个体生活方式、社交关系和职业路径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在身份认同的构建和社交关系的形成上揭示了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的挑战与适应策略。在一直在变化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中,不同的居住地和社交圈子,塑造了一种流动和多样的身份认同。吉登斯(Giddens, 1991)的自我身份理论指出,这种一直在变化的环境促使个体进行自我反思,形成多元化和灵活的身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文化适应能力成为数字游民身份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吸收不同的文化元素来形成独特的个人身份。
不同于熟人社区,数字游民社区的高度流动性难以让数字游民建立持久关系,但他们在不同社区的短暂停留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社区归属感。这种基于共享经历和价值观的归属感可能不如传统社区稳定,但提供了重要的社交支持和认同感。
每次回去都会发现之前刚刚认识的人已经不在了,社区里都是不认识的人。(数字游民佳倩)
×市的流动性特别大,有种相忘于江湖的感觉,即使约个饭都不一定可以约到,今天在这里,明天就不一定了。(数字游民杨雪)
热而且疲惫,我称之为“热疲惫”风格。新冠疫情前我在西班牙考雅思,口试的时候大家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等候,居然没人紧张,都和我热烈地聊起来,毫无顿挫、敏感、腼腆感,聊的时候都和我热烈地目光接触。道别的时候和老朋友一样,这就是“热融感”。我在国内遇到的唯一真诚又不疲惫的中国人,就是那位希腊人长相的笛子手。(数字游民程鑫)
数字游民的流动性与在地性相互交织,反映出个体与地方、全球与本地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的地理套利策略对当地社区产生了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他们在享受全球流动的自由的同时,也寻求与特定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建立联系。全球流动性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不仅在全世界内流动,同时也与特定地方产生紧密联系(Withaeckx, Schrooten &Geldof, 2015)。
数字游民的地理套利策略的实质是在不同地区间平衡生活成本和收入潜力,此现状在经济地理学中被广泛讨论。数字游民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可能对当地社区产生经济和文化影响,如里斯本当地居民就曾抗议数字游民影响了当地物价(Xiao & Wan, 2023)。地理套利在当地人眼里是新殖民主义,对此当地人也有自己的回应方式,涨价是最直接的表现。在×市的菜市场买菜,用不同语言获得的报价略有差异,说普通话的最贵,当地方言次之,当地民族话最便宜。
很多数字游民目的地的承接能力有限,一下子涌入那么多人对当地人造成了特别大的影响,数字游民太多会挤占当地人的公共资源。所以,要以去中心化流动的适应性,来克服集中化脆弱的稳定性。(数字游民杨雪)
我知道买菜是贵的,但我从不讲价,因为我本来就在地理套利,我愿意让他们赚一些,一共就几块钱,其实也贵不到哪儿去。(数字游民黄杰)
数字游民社区更加重视与当地社区的文化融入。D 社区位于大湾村,地处热门景点和城区之间,这里的村民对待外来人态度谨慎,甚至出租房屋时也不会像景区里的村民一样在大门上直接挂牌。主理人李婷向村民介绍美好生活的社区理念,邀请村民到社区喝茶,与村民建立情感连接,获得了在地村民的信任,村民甚至将自家房源委托给她出租。此外,A 社区、B 社区的一些举动,也反映了数字游民社区对融入当地文化的努力。
我想把这个村子做成一个共同的社区。我们把所想要的美好生活状态,通过我们的行为带给他们。现在我要是出去一趟,回来时手上的东西可能都拿不下了,特别是蔬菜,当地村民都一筐一筐地送给我。他们一有空也会到我这边来喝茶聊天,了解我们所做的事,甚至他们也愿意参与。(D 社区主理人李婷)
《经济学人》曾探讨数字游民是否会从小众生活方式转为主流生活方式(Levels, 2020),说明了这一现象对社会结构与互动模式变革的潜在影响。海外市场对数字游民这一新兴趋势的敏感反应,体现在对此群体商机的迅速捕捉和相应商业模式的形成上。多个平台,如 Digital Nomad Academy、No-madlist、Meetup、Remoteyear 及 DNX 数字游民大会等,通过提供工作、旅居信息、社交需求解决方案以及远程工作地点服务等方式,支持并引导了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发展。曼谷、巴厘岛等地的数字游民聚集区及共居社区、共享办公空间的出现,不仅证实了数字游民作为一种生活理念的影响力,也展示了其作为一个可商业化群体标签的潜力。信息技术、零工经济的发展促成了这种新型数字生活方式的兴起,而商业领域的活跃参与则进一步扩展和巩固了这一趋势。
相对于海外,中国的数字游民业态还在起步阶段,只零星出现了几处配套服务。在×市,将“数字游民” 作为标签的共居社区有 4 个,共创空间有 2个,共享办公空间有 2 个。共居社区成员并不完全是数字游民,还有间隔年的学生和处于倦怠期的职场新人。如何持续运营下去,是数字游民社区面临的共同问题。共享办公空间中办公的人很少,某精心装修的共享办公空间开业时,会员价每周 179 元,非会员价每天 39 元,但 3 个月后只要点 9. 9 元一杯的咖啡即可办公一整天;由于进来办公需要脱掉鞋子,老板还给每位客人送了一双袜子。“老板在外地,也不缺钱,已经放弃这里了,现在纯做公益。” (共享办公空间员工李浩)
最早将“数字游民”概念带到×市的 E 共享办公空间在场地到期后没有续租;B 社区进行了新一轮的融资,扩大了住宿容纳量;D 社区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房屋租金;A 社区在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早期通过小额众筹获得启动资金的 A 社区,更加带有试验的底色 “之前有一次开会大概讲了一下运营情况,我听下来感觉是没盈利,且负责运营的同学还往里投了很多,之后应该会半年公示一次财务情况。”(A 社区员工桃子)
×市的乡村同样面临空心化问题,数字游民的涌入是对这些空间的再填充,他们为乡村带来了新的活力和资源,试图建立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市政府引入数字游民考察团,走访各个县,进行实地调研,组织县级政府和考察团成员直接对话,一方面向数字游民展示各个县的人文和地理特色,另一方面希望数字游民代表可以为县级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相关建议。作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灵活工作模式的群体,数字游民的到来可能为乡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数字游民的核心特征是“游”,在于流动,因此数字游民的进入并不能完全解决乡村空心化的问题,他们与乡村的关系往往是短暂的、不稳定的,长期的、稳定的效果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我已经驻村 2 年了,我们有几个老院子正在改建,我们村非常缺年轻人,现在来的人一般住 1 个月左右就走了,最多 3 个月,我们大家都希望他们可以住得更久一点,欢迎他们成为新村民。” (驻村干部张勇)这种短期的、不连续的关系,可能会引起乡村社会、乡村生态的进一步断裂,在这种背景下,乡村地区的发展和转型可能是一种重构,与原有的乡村生态有所不同。“动态的‘切入与接替’带来的是一种辩证的后果,即在否定原有乡村生态的同时,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胡翼青,2024)数字游民与乡村的互动促进了乡村新生态的建立,融合了现代化元素、技术创新和全球化影响。
面对传统价值观和就业压力,数字游民在竞争非常激烈、充满不确定性、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做出了一种新的选择,跨越性地实践了一种替代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安排基于地理流动性和经济自主性的综合考量,其中包含了理想的居住环境、灵活的职业安排以及对社交和社区支持的需求。这种生活方式强调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重要性,并倾向于精神上的满足而非物质上的奢华。因此,关于“数字游民”的定义,不能简单地从经济收入单方面衡量,而应当包含生活与工作平衡可持续、与消费主义脱钩、拥有身份认同和社区感。
某种程度上,数字游民代表一种非主流的文化符号。然而,也有人拒绝这样的标签,他们都以为这个标签下缺乏实质内容,或是对这种生活方式的真实性和持续性持怀疑态度。潜在的数字游民群体对数字游民的想象往往源自社会化媒体上的美好描绘,但实际上这可能仅仅是一种表象,隐藏着早期数字游民通过社群和媒体影响力对后来者进行某种形式的“收割”,从而推动“数字游民”概念的普及和商业项目的发展。在中国,数字游民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如说是一场生活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