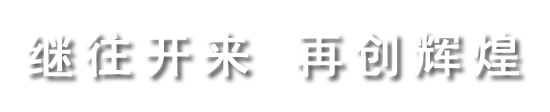美哉藏北高原的湖泊
藏北高原的奇特、美丽和赋有,源于具有许多的雪山、冰川和广阔的草原,也源于那各具特色且漫山遍野的湖泊。
这些数不尽的湖泊颜色奇幻、矿藏丰厚、壮美诱人,犹如镶嵌在高原上的一颗颗灿烂“蓝宝石”。
2001年盛夏,我跟从藏北高原无人区科考团,科考的第一站便是国际上海拔最高的湖泊——纳木错。
驱车从去纳木错,海拔5190米的那根拉山口是必经之处。站在山口,回头是白雪皑皑的雪峰,远看是蓝莹莹的湖水。
“纳木错”是藏语称谓,“纳木”意为天,“错”为湖,意为“天湖”。它坐落念青唐古拉雪山下,西藏班戈县与当雄县的接壤处。按当今的行政区划图,约三分之二的湖面在藏北班戈县境内,三分之一的湖面在市当雄县境内。
纳木错是在第三纪喜马拉雅山运动期洼陷中构成的,其时湖面比现在大一倍以上。因为后期气候的改变,湖水畏缩,现面积仅为1940平方公里。
因为纳木错湖水的畏缩,侏罗纪地层中的石灰岩逐渐显露水面,逐步构成扎西多半岛。后来,湖水仍在不均匀地继续畏缩,因为渐蚀岛上的石灰岩,又构成了多彩多姿的喀斯特地貌。
从空中俯视,与陆地相连的扎西多半岛酷似一头伏在湖中饮水的巨大犀牛,其面积约为10平方公里。在纳木错许多岛屿里,它的知名度最高。
当清晨霞光静静铺洒在海拔7111米高的念青唐古拉雪峰时,这儿是雪山、草原和湖泊的动听国际。雪峰下,纳木错湖水的白色浪花不停地悄悄拍打着岸边,构成高原特有的壮美现象。
俯看湖水,那晶亮透亮、明澈洁白,散落在几十米深的水底的块块鹅卵石,清晰可见。这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美得令人窒息,我不停地按动着手中的相机快门……
在藏北高原陈旧的神线米的纳木错和念青唐古拉是生死相依的夫妻,是藏北牧民心中的“神山”和“圣湖”。
对“神山”和“圣湖”的崇拜,这是藏族自远古先民年代就已开端的,归于藏北的传奇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人们把雪山和湖泊不只神化,一同也品格化了。
牧民们说,念青唐古拉和纳木错在藏北的神界里一个是国王,一个是王后。那座低于主峰的雪山是他们的小儿子,被称为“小唐拉”。
这是在藏北班戈县一侧的纳木错“圣象天门”景象(唐召明2012年8月4日摄)
登上扎西多半岛,首要映入眼帘的是两座15米多高、直径约有10米粗的巨大石灰岩溶柱。两根奇特的石柱规整地摆放在岛前的平滩上,居然相同高,相同粗,还构成一个距离8米左右的天然石门。
咱们在科考中发现,“合掌洞”因其形状像两手相合而得名,洞深4至5米。传说人们进去出来后能够净化魂灵,像初生的小孩相同单纯、仁慈。因为进洞的人太多,此洞壁被冲突的亮光如镜。
扎西多半岛还有一处三洞相连的套洞,中为洞深约15米的“香巴拉洞”,里边的钟乳石叠似层层梯田,洞顶天光一线,亦真亦幻;左洞洞口呈纺锤状,面向圣湖,有天光水影映入,被称为“天堂之门”;右洞伸向山崖的深处,漆黑幽静,令人望而生畏,叫“阴间之门”。
咱们安营扎寨的山脊上有一道百余米长的“玛尼石墙”,因千百年来转湖信徒通过、铢积寸累而成。这墙由刻着经文和佛像的一块块石板和石头垒砌,至今它还在不断地加长加高。
在扎西多半岛一山崖顶上,因为石灰岩的溶蚀而构成一片小石林。远远望去,很像是成百上千名僧人在拜湖诵经。它们造型传神,被人们称为灵物。像这种既有奇沙,又有怪石的天然之物,在扎西多半岛举目皆是,形形色色,不乏其人。此岛被藏族大众称为“吉利岛”,看来与这些天然之物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扎西多半岛还有不少制作在岩洞壁上的壁画。这些壁画以其游牧、打猎等特有的内容赋有魅力地反映了高原人类社会的幼年,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天真与粗糙,但是却表现出一种生动、朴素、富于幻想的颜色。
科考完纳木错,科考团一路向藏北无人区内地前进。一路上最难忘的是一个又一个数不清的湖泊。这些湖泊除水之外,就属盐了。能够说,这儿的盐称得上“取之不尽”。
因为气候的变迁,地壳的上升和湖面的畏缩,这儿一个个近乎干枯和浓缩后的湖泊结晶出丰厚的纳、钾、钙、镁、锂、氯等多种盐类矿藏。
在坐落那曲地区双湖特别区(现那曲市双湖县)嘎措乡以西方向的孔孔茶卡,科考发现,这座近于干枯、海拔4820米的盐湖结晶盐分程度很高,是曩昔藏北牧人驮运盐巴的当地。
历史上,藏北牧人祖辈赶着驮牛或驮羊从这儿挖取食盐运到农区进行“盐粮交流”,唱响了数百年陈旧而又悲惨的驮盐之歌。
相似这种可食用的盐湖,在藏北高原还有肖茶卡、朋彦错、才多茶卡等。这几个盐湖在历史上都是农牧产品交流时期的首要食盐,也是藏北牧民祖辈食用的盐巴。藏北高原无人区科考团组委会主任洛桑丹珍告诉我,这儿边最有名的还属朋彦错盐矿。在西藏农区,人们最喜欢吃朋彦盐巴。因为此盐巴除食用外,还能够医治胃病。农区白叟只要看一眼盐巴就会知道它是不是朋彦错的盐巴。
盐是人类日子和出产必需的食物,关于牧区的人更是如此。它除了食用,曩昔几乎是牧民的钱银,牧民用它来换粮食、茶叶和其它日用品。
这是驮盐队牧民赶着成群驮牛前往藏北无人区的盐湖去驮盐(唐召明1988年摄)
在牧民眼中,一个个盐湖便是一位位大方的女神。每年五六月份,在草原行将返青的时分,专门由壮年男人组成的驮盐队动身了,他们要到悠远的藏北无人区一带,那里的盐湖许多。一支驮盐队,往往有几十上百头驮牛,或是成百上千只驮羊,由一二十名男人骑马带领,一般来回要走三四个月,一两千里的路。这是一次检测人的意志和耐力的远征,充满了艰苦。驮队的牧人每天午后停下来露宿,清晨三点多钟起程。一二个月时刻才干抵达盐湖。
在一个个牛皮袋装满盐后,他们开端回来。其整个行程非常辛苦。眼前是一片又一片无尽的草原,一座又一座雪山,一道又一道河流。裤子磨破了,磨烂了,脚走得又红又肿,前面仍然长路漫漫。藏北民歌《驮盐歌·途中悲歌》唱道:“……我从家园动身的时分,我赶着羊子千千万万。当走过无草无水之地,我心爱的羊子纷繁死去;我从家园动身的时分,我花袋装满酥油肉茶。当步履沉沉踏上归途,我驮盐人吃草喝雪水……”
而现在,这种继续了成百上千年的劳动方法已完毕,许多当地用上了省时省力的轿车运盐。尤其是为消除曩昔的“大脖子”病,有关部门早已明令禁止人们食用这些没有加碘的盐,驮运队连同一同的驮盐文明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界。